在中国体育赛事蓬勃发展的今天,赛场边活力四射的表演群体常被称为“拉拉队”或“啦啦队”,这种看似细微的用词差异背后,实则涉及语言规范、文化认知与体育产业发展的多重议题。从高校联赛到职业赛场,从民族特色表演到国际化标准团队,这一群体的命名争议与功能演变,折射出中国体育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独特轨迹。
一、术语源流:从呐喊助威到专业表演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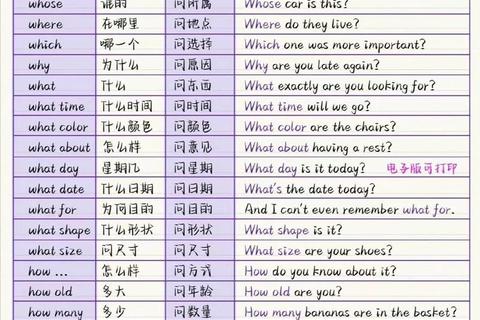
“拉拉队”一词的英文对应词“cheerleading”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末美国校园的美式足球赛场,其核心功能是通过口号、舞蹈和特技动作激励运动员士气。中文语境中的“拉拉队”与“啦啦队”长期并存,前者强调肢体动作的“拉”动性,后者则突出声音助威的“啦”声特征。根据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“啦啦队”为推荐词形,但在体育产业实践中,“拉拉队”因更贴近舞蹈表演属性而被广泛使用。
中国专业拉拉队的规范化进程始于1999年上海诞生的第一支职业团队,而术语的混用现象恰与其发展阶段同步。例如,2001年中国大学生健美操艺术体操协会引进技巧拉拉队时,官方文件统一使用“拉拉队”指代兼具舞蹈与体操技巧的专业团队,而“啦啦队”更多见于非专业助威群体。这种区分在2013年特步大学生足球啦啦队选拔赛等官方赛事中尤为明显,赛事名称虽用“啦啦队”,但评分标准已涵盖舞蹈编排、道具运用等专业维度。
二、文化误读:表演形式背后的认知差异
中美拉拉队的对比常引发“热情专业”与“形式单一”的讨论,这种表面差异实则是体育文化深层结构的映射。美国拉拉队自1880年代起即建立严格的选拔体系,如达拉斯牛仔队要求成员兼具模特身材与运动员素质,并形成四年服役期、禁止与球员恋爱等职业规范。反观中国,浙江“网红拉拉队”等现象凸显出从业者兼职化、选拔商业化特征,约75%的CBA拉拉队员为艺校学生或舞蹈机构兼职人员。
这种差异背后是体育娱乐化程度的阶段性距离。NBA湖人队1979年首创职业拉拉队的本质是将赛事转化为“秀场”(showtime),其动作编排包含弹簧床扣篮等高难度特技,每场表演需调动200种以上队形变化。而中国职业联赛中,直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才出现具备七天编排10支新舞能力的MZ职业拉拉队,多数团队仍以甩彩球、挥旗子等基础动作为主。
三、产业困局:身份定位与发展路径
中国拉拉队的身份模糊性体现在三大矛盾中:一是文化符号的冲突,湖南MZ拉拉队在亚运会融入苗族银饰舞蹈的创新,却被部分观众误读为“民族风与体育不兼容”;二是职业化瓶颈,150人规模的团队中全职从业者不足5%,多数成员需兼顾教培、金融等主业;三是商业价值断层,美国NBA拉拉队员时薪达50-75美元,而CBA顶级团队单场报酬仅500-800元,导致人才储备不足。
这种困境催生了独特的“第二赛道”生存模式。武汉MZ拉拉队通过承接企业年会、音乐节演出获得70%收入,长沙团队则开发出“赛事氛围设计”“青少年培训”等衍生服务。这种多元化路径虽偏离传统定位,却为行业探索出“体育娱乐综合体”的新可能。
四、规范重构:术语统一与标准建立
术语规范化进程与产业成熟度密切相关。2018年教育部《高等院校体育专业术语标准》将“拉拉队”确定为教学规范用语,强调其“拉”字的动作导向性;而文化部相关文件仍沿用“啦啦队”强调听觉元素。这种行政体系内的术语分立,客观上阻碍了行业标准的统一。
在实践层面,三个维度的标准化正在形成:
1. 技术分级:参照美国全美啦啦队大赛(NCA)体系,中国自2021年起试行技巧级(翻滚、托举)、舞蹈级(爵士、街舞)、展示级(道具表演)的三级认证;
2. 职业:深圳CBA赛场明令禁止“夜店风”服装,规定裙摆长度需超过大腿中部;
3. 文化融合:成都凤凰山体育场将川剧变脸融入中场表演,开创非遗体育展演新模式。
这些探索显示,术语争议的本质是体育娱乐产业本土化进程中的文化调试。当“拉拉队”超越单纯的助威功能,发展为包含民族元素、科技交互(如虚拟现实领舞)的复合型文化产品时,词汇的能指与所指必将达成新的动态平衡。
在全球体育产业产值突破1.3万亿美元的今天,拉拉队作为“赛场第二现场”的价值愈发凸显。中文语境下的术语辨析不应局限于语言学范畴,更需放置在体育文化治理、产业生态培育的宏观视野中审视。当MZ拉拉队成员每周跨省训练、南昌硕士生高铁追梦的故事成为行业常态,这个群体正在书写中国体育叙事的新篇章——既是文化自信的展演者,也是产业升级的探路人。
